浓黑似墨的夜晚,窗外零星响起的鞭炮声把刚刚沉入梦乡的女儿吵醒了。为此,女儿多有抱怨。要搁以往,我一定也会在心里轻轻“骂”一声,毕竟是它的突然造访惊扰了女儿的好梦。可那一夜,我居然恼不起来,真的,一点也恼不起来。因为,我知道,这是新年拉开了它最初的帷幕。
不管内心如何慨叹,不管多么不忍不舍,我们还是送走了旧年,迎来了新年。
有时候,感觉岁月真的像一个淘气的孩子,在时光的刀锋上行走。久而久之,那眼角眉梢就有了细碎的皱纹,笑容深处就现出了几缕沧桑。而年,却仍旧似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精灵,任时光飞逝,日月穿梭,它独自沿着自己的轨迹轮回着。
年前,单位里老家在外地的同事给远方的母亲打电话:“妈,我太幸运了,刚才我抢到了过年回家的车票。年三十儿一大早,我就能赶回家了。今年,我终于可以好好陪您在老家守岁了……”放下电话,同事独自坐在卡位上沉默了良久。眼前的那一幕,如同一枚石子落入平静的湖水中,在我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——独处异乡的游子心里蓄积了一年的想念,终于在母亲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得以淋漓地迸发。或许一个人在异乡呆久了,也真的只有在临近过年时,才发现,原来,家一直都在心里,也一直在忙累的打拼中暗自等待着那个关于团圆的契机吧。
和同事相比,我算不上真正的异乡人。我的家乡离我不过30公里,充其量我只是把我的“根据地”从乡村移居到了县城。同事不知道,作为一个本地人,我从心眼儿里羡慕他。他就算离家再远,哪怕倒了火车倒汽车,背着行囊再爬山过梁,也终归会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,那里有父母,有家人,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。而我,早已经失落了那个曾经属于我的家园。
现如今,我在县城内有了自己的住房,有爱人孩子陪伴左右,每天下班只需10分钟就可以回到那里。在外人看来,这怎么都是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是,在我的骨子里,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只是女儿的家,是女儿在多年以后告别我们远走高飞再归来时提及的那个家。这里不是我的家,真的不是。我的家在故乡那个小小的村落,我的家在童年隐隐的梦里,我的家在少年浓浓的思绪里,我所有关于家的记忆都留在那所破旧的老屋里了啊!
不知道是谁说过,童年的记忆足以影响人的一生。对于一个乡下孩子而言,过年总是显得简单而又纯粹,穿新衣戴新帽,提着灯笼放鞭炮。可在大人眼里,过年是一根喜庆的红绳,一头牵着岁月过往,一头系着老人和孩子。记得小时候,每每刚过了腊八,母亲就开始为过大年做准备了——给姐姐哥哥和我每人添置一套新衣,一点点囤积必备的年货,把老屋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。特别是除夕夜里,老屋的周围还会点亮数盏彩灯,站在家门前高高的河堤上远远望去,老屋就像穿了一件崭新的衣裳,别提多亮堂了。
后来,我长大了,在城市里谋生,一到年末便开始魂不守舍,心里就如同长了草儿。放了假,不做片刻停留就开始往家奔,归家的心情急切切的。那时,母亲还健在,老屋也还在,对于已然长大的我来说,与其说是盼着过年,莫如说是盼着那份回家与母亲和老屋团聚的亲情。
再后来,母亲意外地离我而去。此后,老屋不再有人居住,平日里便上了锁。我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回过老家。那天,我执意住进了老屋,没有炉火的老屋。北方的冬天冰凉彻骨,我靠吸烟来驱赶老屋内的寒气,靠内心那仅有的热度来温暖老屋。躺在母亲曾经睡着的位置,我哭了,眼泪大滴大滴滚落至腮边。窗外的风刮得迅急猛烈,扬起的沙尘中带着小石屑敲打着窗玻璃……
转天早起时,徘徊在老屋的前后,我用手抚摸着老屋斑驳的墙壁。堂屋顶上一块新剥落的泥皮砸在锅台上,刺目惊心。那一刻,我才发现,老屋是真的老了。很快,老屋被家乡的哥哥拆除了,翻盖了属于他的新瓦房。倏忽间,维系一个家的纽带便断了……
母亲离去了,老屋也拆除了,那年的春节,我第一次感受了回不去家的滋味。除夕夜里,我在城内的单元房里,独自站在六楼的阳台上,看着各家各户亮起的灯光,看着那些忙忙碌碌喜气洋洋的身影。瞬间,我的心里竟有一种深深的痛感,我忍了又忍,才没让眼泪落下来。
大约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,我明白了,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,于我而言,年是要过的,那个灵魂深处的家却是再也回不去了。好在,渐渐长大的女儿安抚了我内心寥落的过往。于是,每到年终岁尾,我的心底里仍旧有着小小的企盼:唯愿岁月年年静好,好人一生平安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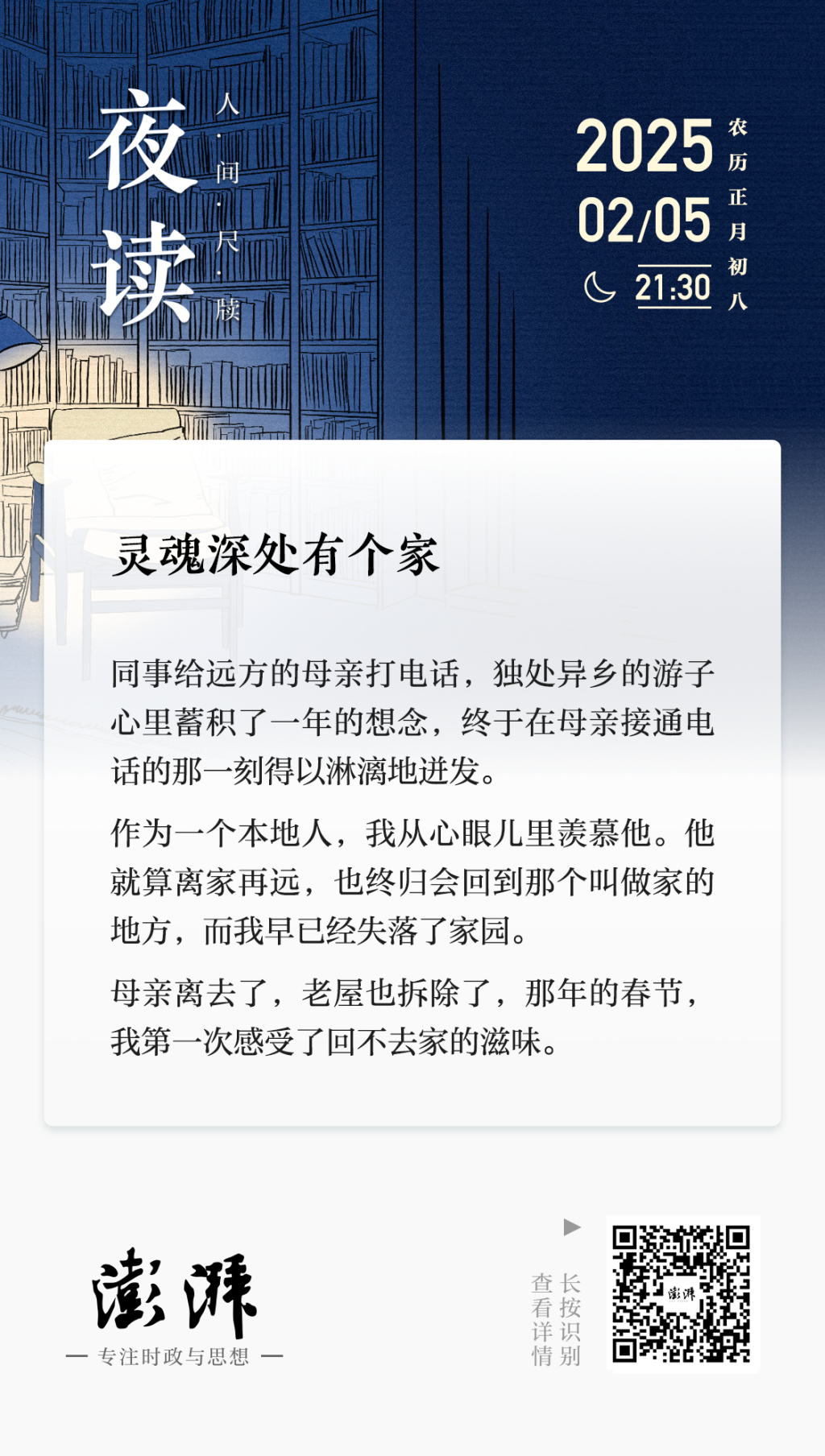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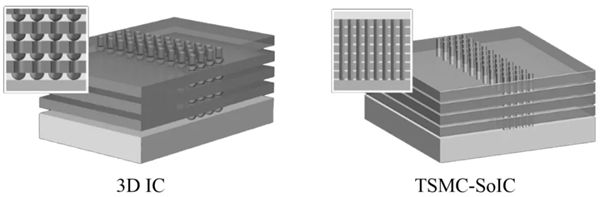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
京ICP备11000001号